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保持年均增速9%的持续增长,还实现了充分就业,分配平等性很高。这也使得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被认为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前20年,日本经济的停滞,曾被广泛解释为美国逼迫日元升值,日本雇佣模式,加之房地产投机的影响。但这种解释明显不足以支撑日本经济活力的丧失。
美国著名的日本经济研究专家、资深财经评论家理查德·卡茨在其所著的《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一书中深入剖析了决定日本经济走向的核心冲突,充满活力的新兴创业企业(瞪羚企业)与根基深厚的传统企业巨头(大象企业)之间的博弈,指出日本在二战后通过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并以此作为主导缔造了日本经济奇迹。但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面对数字化潮流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国际竞争格局巨变,这一模式变得十分僵化。大型企业集团被证明无法适应创新潮流。
不仅如此,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以风险资本支持的初创企业凭借敏捷创新与颠覆性技术驱动的。但日本国内缺乏让瞪羚企业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书中剖析了日本的政策、文化、资本等方面不利于瞪羚企业的不利因素,指出日本经济如果要重获活力,取决于是否能够创造让新兴力量引领变革,并倒逼传统巨头涅槃重生。
书作者指出,事实上,明治维新后的近半个世纪,也就是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以前的增长期内,曾出现过许多具有活力的瞪羚企业。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在二战后,因为美国占领军没有深入进行日本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民主改造,而继续得以留存;战后日本也再度形成良好的培育瞪羚企业成长的环境。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里,还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瞪羚企业获得的是近乎于温室的环境。不仅可以低廉地分别从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引进技术、外包订单,而且这两个时期的日本社会普遍抱以对于企业家探索的宽容态度,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等到这些企业分别在20世纪60-80年代成长为巨头企业后,它们倾向于呼吁保留过去的制度,不愿继续大力探索。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80年代为了加快出口,实现各主要出口产业的规模化,就扶持企业间兼并组合为更大规模的集团,并启用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对之进行补贴和进口保护。这在当时可以理解为权宜之计,但日本政府以及企业界、金融界错误地将规模经济、保护政策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密码。
20世纪70年代,许多出口产业额已经开始面临技术替代,再加上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速,日本政府对此反而设法推行进一步的保护政策来延缓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保护夕阳产业、落后产能不被淘汰。不仅如此,在日本国内,政府也打着防止出现“过度竞争”的旗号,对各类有悖竞争的行为视而不见,包括对违反《反垄断法》的一些做法均没有有效制止。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出口产业在国际上开始面临进一步竞争,日本产业界、金融界与官方共同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政府资金保护下的继续煎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韩国三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实现了对日本索尼、松下等先前领先企业在电子产品领域的赶超。
书中还指出,日本半导体产业等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曾形成对美国、欧洲相关产业咄咄逼人的赶超态势,但最终失去了数字化转型的先机。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美国风险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积极支持企业投资于软件、研发、员工培训、市场营销、组织改进,而日本和欧洲企业依旧投资于昂贵的有形资产。日本企业进行的软件投资比例甚至还大大低于欧洲大陆国家。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就是由政府、军方汇集大量科学家运作实施的,而战后,美国一些知名企业继续延续了研发的规模经济。但书作者指出,进入数字时代后,研发的规模经济效应有所减弱。“随着更廉价的计算机算力、软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大企业在开展研发进而创新新产品和新工艺方面的成本优势要小得多”。相较于美国、中国等经济大国,日本的企业研发活动迄今仍然主要由领先的10家左右的企业巨头实施的,而日本政府投入的研发补贴和税收减免由92%提供给了大型企业,这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是最高的。
不仅如此,相较于美国企业、中国企业,甚至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的公司,日本企业巨头一般并不愿意与本国的初创企业进行项目合作。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几乎每年都有科学家能够荣获诺贝尔科学奖项,但在科学、技术、工艺等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书作者指出,日本经济恢复增长活力,首先,需要进行一场生产率革命。按照麦肯锡2015年发布的报告,哪怕在日本引以为傲的电子和光学设备、工业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先进制造业方面,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还要低29%,比德国低32%。
其次,日本的大企业病在发达国家、经合组织国家中相当显著。尽管日本的劳动雇佣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大幅度的调整改变,但是在大型企业中,仍然沿用终身雇佣,高管就没有职场危机一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利润丰厚的客户群有着很强依赖,没有动力去投入或支持投入创新。
第三,创造有利于瞪羚企业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这就需要打破现有致力于保护落后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从政策上关注瞪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书作者在书中批判了饱受争议的日本“安倍经济学”,指出其本质上还是通过政府财政刺激以及承揽企业、金融机构的债务,来为大企业集团解困。不仅如此,要让瞪羚企业更好地涌现,在日本现有经济环境中,可以通过政策指引,鼓励企业内部培养创新团队、创业企业家。
总的来说,《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这本书比较深入地剖析了人们常说的“日本病”、“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书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日本战后超长增长的动能,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精神的成果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名噪一时的多家企业巨头,却劫持了日本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成为了既得利益捍卫者,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延续了创造性破坏这一推动增长的核心力量。这些问题在工业经济时代向着数字经济时代转型过程中,其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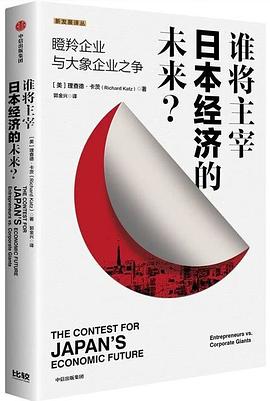
书名:《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
作者:(美)理查德·卡茨
译者:郭金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9月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973号